照片提供/印刻文學
撰文/夏曼.藍波安
蘭嶼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從一封寫給妻子的家書回看四十年來的記憶,由家族、傳說、祭儀、海洋孕育出的文字,與成長過程各種經驗碰撞,苦澀青春,生活甘苦,邊陲異質,在現實和夢想的漂泊之間來來回回,一次次出走,一次次歸來,匯聚成優美的《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一書,在此與季刊讀者分享海上的美麗。
船,它存在於有河、有湖、有海的各個角落,於是產生了河流民族、湖泊民族、海洋民族等等的。這些民族從最初的原創開始了與河流、與湖泊、與海洋編織成的許多故事,敘述著人們數不清的水與船的想像。星球裡每個區域,大小不等的地方,強勢、弱勢等民族在不盡相似的樹林植被,氣溫也研發出不盡相似的船貌。船貌如何如何的,也是敘述著船與河流、湖泊、海洋的故事,同時人類也造就了船的使用性,以及船隻衍生的生活美學,還有船的神話。

對於我,神話的美,在於人們把幻覺幻象成為事實。相傳有兩位兄弟用石斧花了很長的時間建造自己的船。哥哥的船底是平面的,弟弟的是現今達悟人承繼的船身、船貌。兩艘船透過海洋、波浪的考驗之後,證實了弟弟建造的船是利於遠航、切浪的,又兼具視覺上審美的感覺。
象徵希望的火炬,一把即是一艘獵魚大船
一九七○年代前,我們這些戰後出生的新生代,在飛魚招魚祭典,我們就知道自己是屬於那個獵魚的漁團,每個漁團在飛魚季首月的夜間,船內皆裝載著數把的乾蘆葦,以及裝在甕裡的木炭。我們這群小孩為此在夜間常常聚集在我大伯家的涼台,或是庭院。漆黑的海面是沒有月光的照明,一把火炬、兩個火炬……每個火炬代表一個十人的獵魚大船。數十個火炬浮生浮沉的在我部落前的海域放光明,火把隨著正在漁撈,正在划槳的生、滅。
漁夫們憑藉個體舵手的獵魚經驗移動船隻,火炬在再次點燃、再次熄滅的隨興,對我卻是生之火的希望,給我萌芽的心魂刻下莫名的愛慕,還有更多的渴望自己是其中的一名漁夫。
冬末的雲片遮蔽了天空的眼睛,風來自於部落的北邊,在黑夜,每一天的黑夜,遙遠的海平線幾個微明的漁船燈光,有時候十幾盞,有時候三、四盞,與近海的火炬,讓我從小就可以辨別出兩者間的差異。

有燈的船是機械船,可以在海上過夜好幾天,或者一星期,在船上可以煮飯燒菜,以及靠雨水洗澡,我認為那也是很美的一件事。我或許出生在小島,當時一個未被現代化困擾的地方。到B部落需要用走的,收成的地瓜要扛,要走路,一切的一切盡是人力,腳掌手掌似是身體的發動機,只能在有限的距離活動,包括船隻。火炬的船是人力雙手划的船,當黑夜的海上的火炬熄滅之後,祖母禁止我們這些小男孩去海邊迎接我們的父親們的回航。
出海!實現兒時的夢想
我一直在思考祖母的話,「禁忌」,我當時約莫六歲。一九九一年的二月某夜,父親兩兄弟,兩位堂哥,三位表叔,以及已經三十四歲的我,划著八人八槳一舵的大船出海了。這是我兒時的夢想,喜悅當然存在心海,就像記憶存在腦海一樣。與我兒時不一樣的環境是,我原來的部落已經有了路燈,光明了起來,繁星明光被路燈取代了「光」的意義,彼時四十六歲正值壯年的父親,當下此刻他已經是七十四歲的老人了,那一夜,父親掌舵。
遠離了部落的路燈,我們划的船駛經到了比黑夜更黑暗的沿岸礁壁,除去心臟跳動的怦怦聲以外,只有槳葉插入海裡節奏一致的聲音讓船隻行駛,我的二頭肌、三頭肌,我握槳的手掌漸漸的結實了起來,浮動的海面來自海底跳躍的湧浪,然後拍擊礁岸回波震盪讓船隻起伏,好舒服,我心裡想著,我終於出海,也即將點燃蘆葦的火炬。
大海的語言,陸地的語言
有種美感悄悄地滲入我心,從第一槳、第十、第一百、第五百、八百槳,我們或遠的、或近的划,離岸約莫二十公尺、五十公尺、一百公尺閉嘴不語的旅程,船隻如是幽靈船的感覺,說一句話是美的,好像跟海浪說話,跟古老的漁夫們,我兒時眼前的真男人,他們在海上說的語言,諸如轉彎的時候,說「切魚肉的一邊」、火把「順著風的路」、「槳支在拍手」是距離岸邊不遠也不很近,說十句都是男人們在海上的語言,但我一句也聽不懂。
原來飛魚季節首月在海上獵捕飛魚,直述句,如「這裡有飛魚」是最大的「禁忌」,必須說「銀白的鱗片」,許多許多的,我民族的語言因為飛魚神的神話故事的典故,在海上與陸地的語言必須「分類」,島嶼不會移動,海浪會浮動(性情不穩定)。
因為自己的語言我卻聽不懂,我感覺了那種潛在的美感,像是人類在海上獵魚的爆發性永不可能超越海浪暴怒的爆發力。在黑夜的海上,人們的安靜是回應外海的海浪的安靜,說話時是回應海浪拍擊礁岸,海浪跟陸地說話輕重表情。我回家,與前輩們共同划著木船航行,每一槳划船的感觸,對於我就是每一頁的活的教科書,訓練腦部思維,也是體能的訓練,更多地每天改變的海洋知識;風、雲、雨、月、波浪、潮汐、洋流,還有心靈感悟。

與前輩們划船回航,每一槳都是海洋的文學,自己的故事,在海面上,星空下;在海面下,水世界的魚類世界,也只有依賴自己的心魂、自己的身體是唯一接近「海的心跳」的路,那是沒有捷徑的路、方法。我如斯說。
寫作的啟示:我們住在「不同的星球」
「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起初是我在《幼獅文藝》月刊連載的文章篇名,但我忘了是哪一年的連載,也是我唯一完成的「連載」成績。我寫這句話的同時,其實過去的《聯副》、《中時副刊》也都曾經邀我寫一千字以內的「連載」文章,對我而言,雙週一篇,那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困難的是,我居住在西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上,小島的生活作息瀰漫著海洋的浪漫,瀰漫著學習島嶼的生活,諸如潛水獵魚,巡山,尋找造船的樹材,學習島嶼民族植被生態的知識,沉溺於夜航,划船捕飛魚,或者在海上通宵獵魚,或者跟長者閒聊島嶼物語,於是感覺時間飛逝,往往無法專注於書寫連載的故事,而半途逃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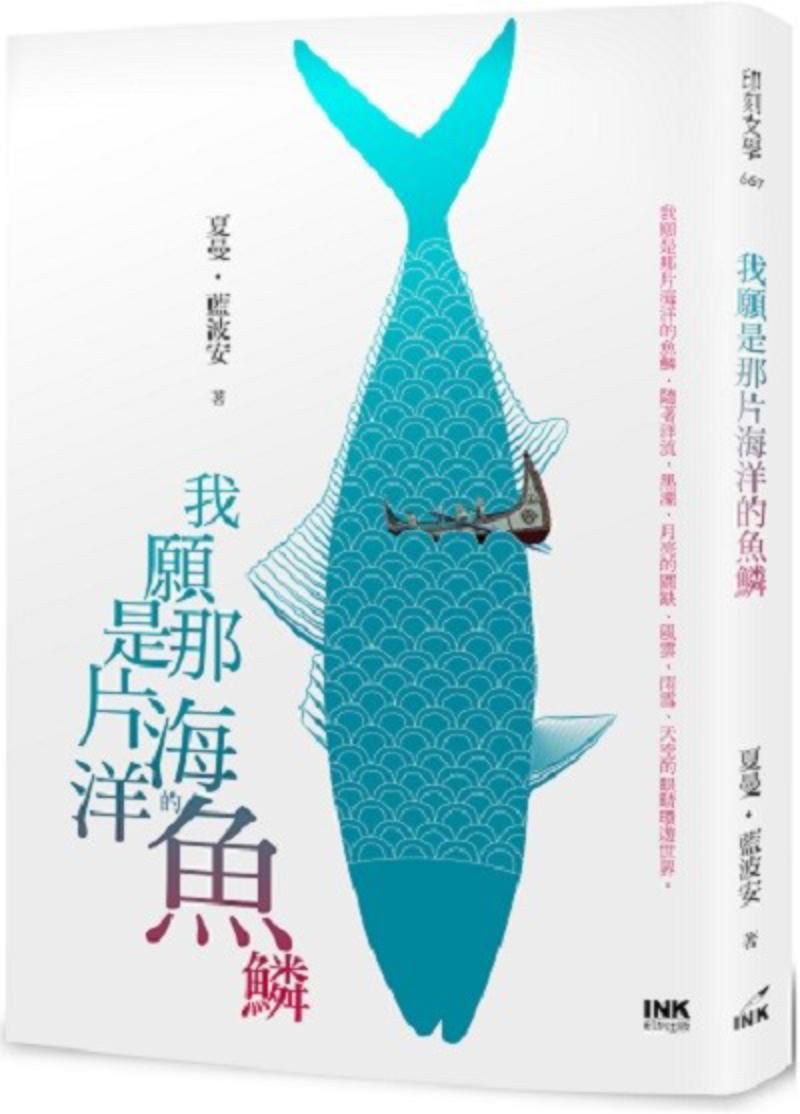
當下的此刻,回想起來都是我的錯,錯在我試圖思索運用城市的思維語法,城市的書寫模式,於是下筆起來五音不全,牛頭不對馬嘴;錯誤在於我說的族語愈來愈好,阻礙了我原來就不好的華語書寫的進步,原來就不符合「漢式作文」語法句型的文章,或者我寫得跟城市無關的事物,太在意城市人的感受,我錯了。我想說的「小島的宇宙」,正是城市街燈的邊緣,此刻我更想說明的是,我們住在「不同的星球」:簡單來說,我把連載專欄複雜化了。
對於我個人,或說自稱是「海洋文學家」,理論上,我其實並沒有十分認真地思索這個「頭銜」的實質意義。依然記得,我在一九八○年大一的國文必修課的作文課,老師給班上打的作文分數,幾乎都是在八十五分以上,然而給我的分數,卻是六十七分,老師用紅筆的評語是,「我看不懂你在寫什麼?」
我民族說故事的核心:
魚類、天空、風雲雨、海洋潮汐、陽光月亮
一九九九年的《黑色的翅膀》由晨星出版的時候,有位女性作家評論這本書的前兩章,說「不是小說的書寫劇情的方法」。又《天空的眼睛》(2012,聯經)的編輯說:「希望把浪人鰺的話語敘述換成『我』,也就是說,以『人類』為主述者。」我當時即時的反思是,「我們住在不同的星球」,我為何必須依「你們」(城市文學)的標準為書寫的標準骨架。假如我可以說,「我們住在不同的星球」,我們的宇宙觀是不同的,在蘭嶼的我們,魚類、天空、風雲雨、海洋潮汐、陽光月亮是我民族說故事(文學)的核心,你們城市的街道巷弄的故事,其實就是我們民族眼前的大海潮汐,以及調皮的各種魚類,換言之,我的出生是說我的族語,而非華語,我的族語讓我認識原初的大海情愫,華語讓我認識世界的文學、華語文文學。
回想一九九七年的《冷海情深》(聯文)的出版問世,那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如今我稍稍地再重讀的時候,發現我的華語書寫,敘述確實有許多的缺陷。二十四年前,我已是四十歲的人了,那是我個人與海洋的戀情故事,日日沉溺於波浪下的水世界,方感悟出,那就是我民族每一位男人的海洋小說,也才感受到我們在海裡的身體是優雅的。
「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我身體的鬥志已經沒有當年的豪氣膽識,但我依舊徜徉在大海的懷抱裡,沁入海裡的溫情,我並不知道這本書的書寫可以給讀者什麼樣的感觸,無法預期。
我只能說,我會繼續的努力書寫我所認識的「星球」,也懇請讀者們給予我支持,以及深層的鼓勵。
特別説明
原文收錄在2021年12月印刻出版的《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感謝印刻出版鼎力協助,同意轉載。
連獲日本鉄犬異托邦文學賞、吳三連文學獎、臺灣文學金典獎之後,夏曼.藍波安獻給家人和讀者,美麗的、波動的螢光鱗片。
夏曼.藍波安
1957年生,蘭嶼達悟族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集文學作家、人類學者於一身,以寫作為職志,現為專職作家,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的負責人。1992年《八代灣神話》獲中研院史語所母語創作獎,1999年小說《黑色的翅膀》獲吳濁流文學獎、中央日報年度十大本土好書,散文《冷海情深》獲1997年聯合報讀書人年度十大好書、《海浪的記憶》獲2002年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漁夫的誕生〉獲2006年九歌年度小說獎,並為同年第23屆吳魯芹散文獎得主,並以《老海人》獲2010年金鼎獎。2012年《天空的眼睛》獲得該年度中時開卷好書獎。2014年《大海浮夢》入圍2015年聯合報文學大獎,2018年獲得日本鉄犬異托邦文學賞。2017年獲得第40屆吳三連文學獎,2018年獲《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評選為臺灣當代十大散文家。2019年《大海之眼》獲臺灣文學金典獎,及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
本文轉載自《新北市文化》季刊。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