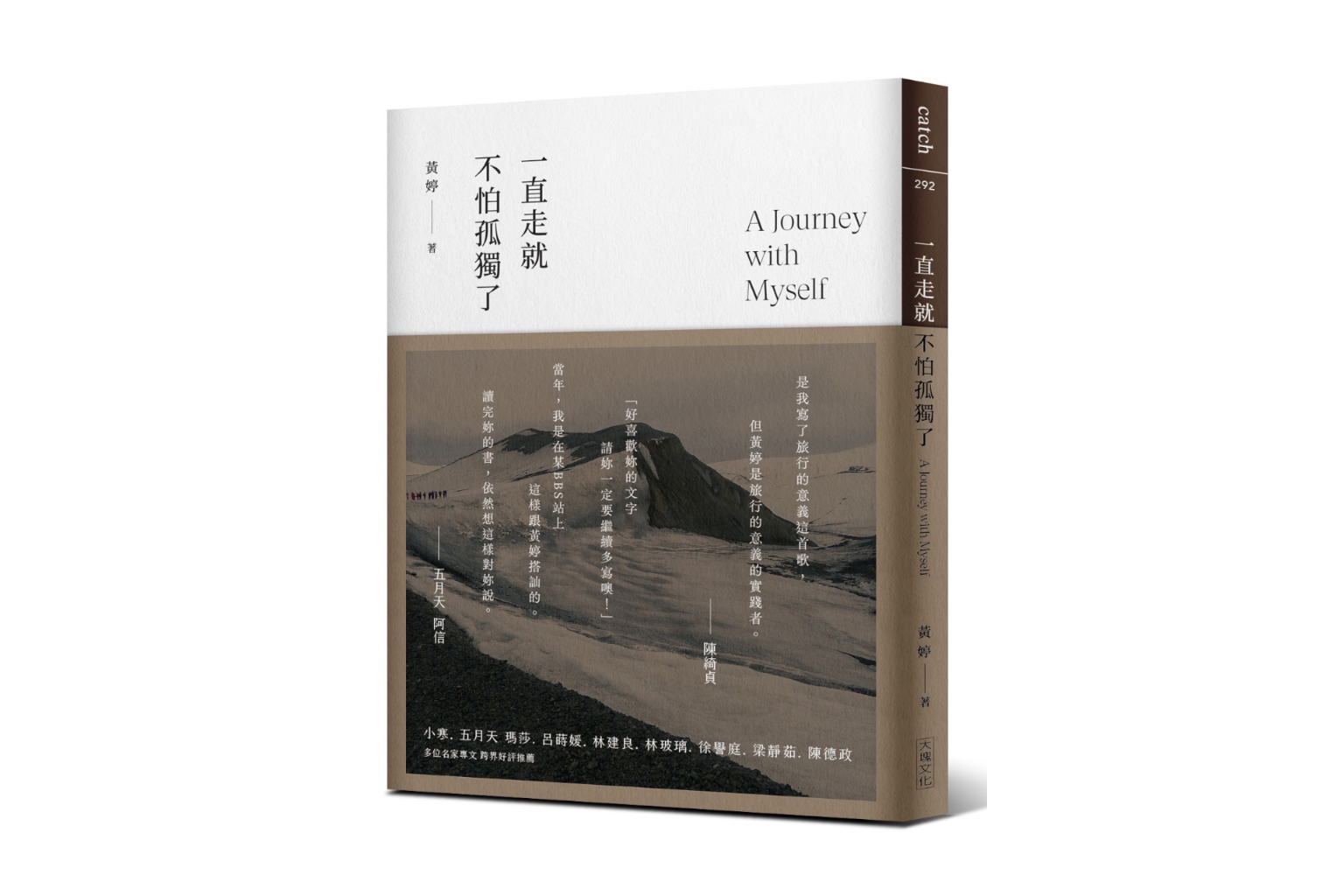2017年4月,兩位從台灣到尼泊爾登山的青年梁聖岳和劉宸君,遇到大雪,被困在山洞裡47天之後,梁聖岳獲救,劉宸君不治。有人問歷劫歸來、體重剩下三十公斤的梁聖岳,重來一次,還會登山嗎?據說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會,而且會帶著女友前來,因為「那是她喜歡的事情。」
為了一件喜歡的事情,可以堅持多久,該堅持多久?
出發前我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這晚,在海拔四千多公尺高的丁伯崎(Dingboche),深黑的夜幕席捲山屋,近零度低溫鑽刺皮膚,全身毛孔都像被細針挑起來,拉得緊緊地像隨時要崩斷。我的雙腿僵硬、膝蓋劇痛著,整個人蜷縮在已難以顧及髒污的睡袋裡,臥躺於冰冷陌生的硬石床上,想著無法繼續,想著這會是哪一部低成本電影的結局:一個從沒爬過一千公尺以上高山、卻失心瘋想走上超過五千公尺高的喜馬拉雅山脈的女生,自以為要寫下什麼驚為天人的勵志故事,結果中途廢了腳,宣告挑戰失敗。當一趟要花三萬美元的直升機降落在停機坪,將她抬下山前,她淚灑聖母峰的山腳⋯⋯
剛認識不到一星期的夥伴,用無條件的溫暖將我包覆
我想著這結局,最終大約只能換來零星觀眾的訕笑,電影不僅連院線都排不上,數位平台可能也沒人要,人們偶然從網路上下載到畫質粗糙的盜版版本,在颱風天配著泡麵、漫不經心地看完。
從小不是一直喜歡閱讀偉人傳記嗎?傳記裡都是成功的故事,我的人生怎能成為這失敗電影的主角呢?
這是EBC健行的第五天。清晨從Tengboche出發,繼續上行,就著眼前千篇一律的景色,身體裡堆積的疲累感不知何時已燒光出發時的熱情,低潮無預警地乘隙而入,心情沒來由的悶,極度厭世,腳步千斤重,一千一萬個不想走,也不想講話,孤僻魂上身,怕被隊友干擾,於是就儘量在隊伍裡落單。
可這一落單,開始什麼都不對勁了。左右兩腳的膝蓋外側劇痛,每踏下一步都是由膝而上、貫穿心臟的痛楚。勉力走了一個多小時之後,痛感快速擴張,左膝已很難彎曲,一彎就痛到彷彿全身都要散掉,無論做什麼拉筋、伸展,都毫無幫助,一步痛一步,每走一步都用了全部力氣,都像是被人用鐵錘狂敲一次膝蓋。
才走了第一個小時,我不敢想路途還有多遠,只能眼望地下,一拐一拐走,用相對比較不痛的右膝來前進,拖著僵直的左腿。
該怎麼辦?我唯一能依靠的雙腿,廢了。一路拖著步伐,感覺每一步都像用盡最後一絲力氣,巨大的恐懼一波波掩過來,鋪天蓋地。我一個人,如果走不下去,在這幾千公尺的高山上,離家數百哩,該怎麼辦?該怎麼辦?
胡思亂想的徬徨間,隊友們一一跟了上來,發現了我的狀況。他們聚集在一起,商量對策。
我帶的登山杖只有一根,小麗毫不猶豫地把她的兩根遞給我一根,說:「兩根比較好支撐。」
小蔡脫下她的護膝交給我,說她沒關係,先把我的腳養好再說。
阿凱已經不吐了,除了頭有點暈,他說我的肌肉緊,有可能是體內電解質不平衡,所以就幫我泡了一大壺寶礦力。
阿秋找出所有手邊可能有用的止痛藥、肌肉鬆弛劑,妮可教我拉筋的方式,懷疑是ITBS(註)的問題。當時我並不明白那是一種膝蓋長期摩擦之後常見的傷,是要到後來投入馬拉松運動之後,才漸懂得。
註:髂脛束症候群(Iliotibial Band Syndrome, 簡稱ITBS)。髂脛束是連接股骨外上髁(大腿)和邊脛骨(小腿)之間的韌帶,又長又粗,隨著膝蓋彎曲、伸直的運動被往前、往後拉扯。當膝蓋反覆運動,髂脛束與股骨外上髁不斷摩擦,發炎而產生疼痛現象,即為ITBS。簡而言之,ITBS是由髂脛束反覆穿過股骨外上髁所產生的傷害。
從來沒有習慣麻煩別人,遇到任何難題的人生,都是自己解決。此時,我也以為會一個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災難,會一個人倒下或投降,萬萬沒有想到,這些剛認識不到一星期的夥伴們,用無條件的溫暖將我包覆,前路漫漫之際,卻每個人都給了我他們身上在健行中最重要的東西。
只要再撐三天就到山頂了,放棄與不甘心在耳邊糾結
這些溫暖,帶來了無形的力量,讓我感到自己並不孤獨。懷著感恩,吃了藥,拉了筋,包好護膝,撐起兩支登山杖,喝掉一壺寶礦力,繼續上路。
持續著時好時壞的痛楚,但跟著周圍的所有支撐,心重新被注入了勇氣。我想:至少在這段路不能拖累大家,至少我要好好結束今天。就這樣,咬著牙,走到今日的終點Dingboche。
晚餐後,獨自回房躺在床上,高海拔的缺氧使我感到暈眩,雙腳像根棍子般僵直而動彈不得,聽外面傳來人們的談笑,想劇情怎麼會這麼急轉直下?昨天在抱怨辛苦之餘,起碼還能走,現在連能不能站直都是問題。然而,已經五天了,眼看只要再撐三天,就到山頂了。難道要在這裡停下來嗎?身體的痛楚襲擊著我的意志,出發前向著父母信誓旦旦的笑容,臉書上意氣風發的宣言,那無數的讚與加油打氣的留言,此刻在腦中漸漸褪色而轉為一個嘲諷。
我耳邊糾結著兩種聲音:放棄,不甘心。
放棄是解脫,雙腳得以安歇,從此不用再經歷那些走不完的台階,看不見盡頭的山坡,也不用再爬得一口氣提不上來、整顆心揪得感覺血管快斷了時,還得承受兩條腿筋曲折拉扯的劇痛。更不用再持續那些內心裡無盡的自我懷疑:為什麼我會在這裡,為什麼我要折磨自己,為什麼山路好像都走不完,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放棄吧,就不會再有那些為什麼,就能好好睡一覺,看書寫字吃飯仰望群山,躺在這床上靜待隊友回程下山就好。
放棄,就能終止一切痛苦,回到舒適圈,多好。
放棄吧,放棄!這聲音拽著我,幾乎就決定要跳下床,把這個想法告訴領隊的魚大和阿秋。
可是,另一個執拗的我,不甘心啊!
不是應該要寫勵志故事嗎?「文武雙全,征服EBC的作詞人」的勵志故事啊!怎麼到頭來會變成一場鬧劇收尾?
想像著夥伴們經歷千辛萬苦,終於流著淚登上飄雪的聖母峰基地營,寒風中,在石碑旁插上國旗,然後拍下那張留存一生、流傳給後世子孫的照片裡,沒有我。
想像著夥伴們夜夜在爬山的筋疲力盡之後,於山屋裡群聚聊天,共享一餐歷劫歸來的幸福,那溫暖的情境裡,沒有我。
想像著幾年後,夥伴們在臉書上回顧這段日子,回顧那些一起走過的影像,在他們滿滿的由艱苦轉為甘甜的回憶中,獨缺一個我。噢,有我,只是我將在他們記憶中成為永恆的「那位中途停止、沒走完的人」。
這是一場和自己的比賽
而也許比起這些,我更不安的,是下山以後繼續延伸的未來人生裡,自己都將用怎樣的遺憾來回顧這個放棄。往後每當想起這段EBC之行,記憶裡都將只有五日爬行之後的鎩羽而歸,只有獨坐山屋的悵然,看那大山的角度,也與以往並無不同。而這種遺憾,再也彌補不了,即使是未來有機會再上山,也已人事全非。
我已非當時的我,而當時那個停下腳步、半途而廢的我,永遠在記憶中駐紮了。
天人交戰。「如果現在放棄,比賽就結束了。」從小看的熱血漫畫《灌籃高手》裡,胖胖的安西教練言猶在耳,可前路茫茫,腳上的劇痛沒有半點消減,明天,我真的走得下去嗎?
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上,每一口呼吸都快要窒息,往前走也不是,後退也不是,要求救都不知道能找誰,在侵蝕進五臟六腑的低溫中流下眼淚,這是我人生最無助的時刻之一。
室友妮可拿了冰袋進來,幫我綁在膝蓋上冰敷,然後拿出一小瓶類似萬金油的東西,為我抹上額頭。她說,好好睡一覺,明天會好的。
這是一場和自己的比賽。在過去的人生經驗裡,每一次這樣的比賽,我都臨陣脫逃,一走了之。反正放棄,總是最容易的。何況這場比賽,沒有遊戲規則,沒人拿槍抵著我比下去,想怎樣,都百分之一百是自己的決定。
躺在床上胡思亂想,忘記是怎麼睡著的,只記得睡前下的決定是:「放棄吧!不要勉強了。如果因為我的傷而拖累大家,不是更不好嗎?」以這樣的體貼作結,當一個不麻煩別人的人。
事實上,我根本分不清楚這是藉口還是為別人著想,但真的太苦了,明天醒來,我無論如何不想再走了。
Day 6: Dingboche丁伯崎 (4260m))高度適應
聖母峰馬拉松
一場昏睡,彷彿過了一世紀,一世紀的天人交戰。清晨六點,在冰冷的空氣中醒來,太陽如常升起,又是山上的一個大好晴天。
咦,腳不痛了。完全不痛了。我下床走了幾步,順順的,這雙腿完全屬於我。昨日的所有痛苦掙扎都像是場惡夢,在光天化日之下,消散無蹤。
睡著之前,在萬念俱灰中下定決心:不再走了。打算就停在這裡,等夥伴下山。還說服自己:身體要好好保養,不可勉強。然而現在睡飽醒來,不痛了,健步如常,我又陷入了猶豫⋯⋯其實不只腳傷,也好想念台灣的朋友,想念鹹酥雞和滷肉飯,想念我的小窩。而且現在好了,不代表上路之後不再出毛病;是不是維持原案,停在這裡就好呢?
放棄容易,繼續才需要勇氣。我已沒有勇氣,也想不出前進的理由。然而,看夥伴們一個一個收拾好行裝,背上背包,準備上路。他們的笑漾在背景是覆雪大山的圖像裡,將要迎向充滿鬥志的一天,那一刻,我又突然自慚形穢,好想走進那圖像之中啊。
阿秋來關心我的腳傷,我說沒事了,她問我要休息嗎?我抬頭看她如常純淨的雙眼,說:「我去拿背包,我要上路。」這回應完全沒有經過大腦,但,管他的。或許不經過大腦的決定,才是身體真正想要的決定。
繼續上路。加入夥伴的行列,一股莫名的趨力又在體內燃起:我要向前走,登上聖母峰基地營。
我們在Dingboche多停留一日,做高度適應。今天必須爬到住宿旁的山坡上,一個插白旗處,4750公尺。腳力如常,只是心中帶著痛楚復發的恐懼,恐懼其實無用,我努力甩脫它。路上看到一些喇嘛在山的稜線上行走,光禿禿的山岩中,點綴著他們的修道屋。簡陋的水泥山屋,在滿是石礫的山上矗立,四周什麼都沒有。無處擋風,無處躲雨。單這光景,就能感覺到生活的艱辛。幾座佛塔散佈著,五色旗飄在風中。
這海拔高度,早已沒什麼植被,除了短短的雜草之外,就是光禿禿的石礫路。周圍被雪山環抱,抬頭是萬里無雲的藍天,世界彷彿只剩下天與地,與一步一喘的零星人們,別無其他。
途中遇到一位戴墨鏡的雪巴人,身上穿著印有第十屆「Everest Marathon」聖母峰馬拉松的T恤,看他黝黑的皮膚與精實的身材,我不懷疑他跑完了這場世界海拔最高的馬拉松。
創立於2003年,聖母峰馬拉松是為了紀念首次攀登上聖母峰的尼泊爾人丹增諾蓋和紐西蘭人Edmund Percival Hillary(在紐西蘭五元鈔票上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登頂五十週年而設立。他們在1953年5月29日完成了站在世界之巔的壯舉,因此馬拉松的日期也訂在每年5月29日。
當第一次聽到聖母峰上也能跑馬拉松時,我瞠目結舌。氧氣稀薄、路面顛簸、高原反應隨時無預警來侵襲,每一寸路我都舉步維艱、呼吸困難,是要如何「跑馬拉松」?這一路上,我們的行李都是由雪巴人幫忙揹運,流傳著許多關於他們「呼吸系統與平地人不同」的傳說,因此也不意外,每年聖母峰馬拉松的奪冠者,都是雪巴人。只是依然太難想像,在這世界之巔「奔跑」的光景。
這場馬拉松的參賽選手,要先花十多天從盧卡拉步行上聖母峰基地營(就跟我們這次健行的行程一樣),接著才以EBC為起點,往下跑到南崎巴札是為全馬,跑到此刻我們所在的Dingboche,則是半馬。
上山已經夠累了,還要用競賽的方式跑下山,歷經起起伏伏超過七千公尺的海拔高度,這過程,該比我這緩慢的健行路途,艱辛十倍吧。我這樣想。那麼昨天一日的小小ITBS發作,又算得了什麼呢?想起陳彥博跑超馬的紀錄片,他那些裂開的肌膚、面色蒼白仍屹立不搖的決心,我又再度激勵了自己。
聽說來跑聖母峰馬拉松的人,多數不是為了競賽,而是追求一個完成自我的目標。是啊,在這連呼吸都困難的環境裡,跟誰爭強鬥勝都已經失去意義,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突破自我。自我是每個人生命中最高的山,沒有確切的高度數值,沒有登頂的時間表,也無人同行。
登山者沒有不孤獨的。可也只有孤獨,能帶我們穿透生命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