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2019年臺灣風靡著《返校》這句經典台詞,這部電影設定在仍處於戒嚴時代的1960年代臺灣,劇情召喚白色恐怖幽靈,闡述倖存者不敢、也不願回想的那段歷史。
然而,距離臺灣幾萬公里外的愛爾蘭島上,也同樣存在著當地人不願面對的過往,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林玉珍的研究重點便是1920年代初期愛爾蘭慘烈的獨立戰爭和內戰,及其後續的記憶創傷。
從博士論文研究喬伊斯(James Joyce)開始,林玉珍便與愛爾蘭脫不了關係。走在研究的道路彷彿拿著哆啦A夢的放大縮小燈,從微觀的文本研究,到宏觀的歷史脈絡,最後鎖定《暮氣沉沉的國度》(No Country for Young Men)、《在黑暗中閱讀》(Reading in the Dark)、以及《秘密經文》(The Secret Scripture)三部小說。國家彷彿是有血有肉的人類,經歷極大傷痛之後也會跟著鎖住記憶,努力不讓傷口暴露在空氣中。即使到了1990年代的愛爾蘭,人們依舊對於一甲子前的創傷噤聲。只是愈是不說清楚,就愈容易挑起人們的好奇心。
「愛爾蘭在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並未成功,1919年英國發動英愛戰爭(the Anglo-Irish War),兩年後雙方簽訂協議,北愛爾蘭成為愛爾蘭獨立與和平的籌碼,也激起國內主戰派的怨恨,全國陷入非常時期。」林玉珍嘆道:「這與歷史上以恐怖統治震懾人民的極權國家同出一轍,即使枕邊的親密愛人也可能瞬間變成敵人,輕則排斥、重則清算的方式對待異類,導致許多當事人的家屬或後代只能噤聲,身心靈也受到或大或小的影響。」
傷痛過去60年後的今天,愛爾蘭似乎更著重於拚經濟,「克爾特之虎」(Celtic Tiger)的經濟大起飛榮光讓愛爾蘭擺脫殖民地的印象,看在建國初年受害家屬的後代眼裡,可能並不是滋味。1990年代後興起的創傷小說,或許也是要提醒愛爾蘭人不能遺忘國族記憶。
跨世代的塵封歷史
林玉珍以愛爾蘭現代主義作家詹姆斯·喬伊斯於1922年出版的小說《尤里西斯》(Ulysses)的一句話:「歷史……是我試著從中醒轉的夢魘」為引言,點出愛爾蘭歷史中的暴力,不僅存在於當下,其效應甚至影響至現代,成為愛爾蘭人試圖醒來卻依舊沉睡的掙扎。
林玉珍透過三本小說,包括薛摩斯.狄因的(Seamus Deane,1940-2021)《在黑暗中閱讀》、席巴思欽.薄瑞(Sebastian Barry,1955-)的《祕密經文》,以及茱莉亞.歐惠倫(Julia O’Faolain,1932-2020)的《暮氣沈沈的國度》,探討成年或遲暮之際的主人翁,回顧幼年或青年時期經歷愛爾蘭內戰期間的創傷經驗,亦即透過個人生命故事,映照愛爾蘭現代史。
「我採用心理分析與創傷理論,深入分析小說主角的心理狀態與國族傷痛的關聯性。」林玉珍指出,當人們遭遇重大傷痛時,瞬間無語也不敢對他人傾訴,於是祕密被埋在心房密室,經過時間淬鍊打造出「集體墓室、社群墓室、甚或國家墓室」,裡面囚禁著跨時代幽魂(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
一代傳一代的傷痕
.jpg)
《在黑暗中閱讀》於1996年出版。敘述愛爾蘭1945至1971年之間的生活風貌,內容雖與作者薛摩斯.狄因經歷重疊不少,但狄因否認這部作品是回憶錄或自傳。另一方面來說,作者將自身經驗放大為國族歷史,迂迴呈現愛爾蘭內戰時期的共有創傷記憶,以揭露先輩無以言傳的祕密,進而梳理個人和集體的「幽魂效應」。
《在黑暗中閱讀》裡,敘事者長大後挖掘上一代的過往,卻是一場七零八落的拼圖遊戲,他始終無法得知艾迪伯伯的行蹤,長輩彷彿水蒸發似完全消失於這個世界。當父親好不容易提到「失蹤者之地」的傳說時,主角便問:「艾迪的靈魂,是否就在這裡為失落的出生地哭泣,我納悶?」於是一切又成為不可言說的秘密,探索歷史就像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閱讀。
敘事者轉向母親,她絮絮叨叨的情話裡,指涉的對象並非自己的另一半,而是另有其人,於是「背叛」的主軸從父母親傳到孩子身上。如雜草蔓生的過往降臨在敘事者身上,延伸出對警察的仇恨。敘事者抽絲剝繭,極力找出艾迪失蹤的真象,直到父親說出:「他是個告密者,被自己人殺掉的。」才終於揭開了真相:艾迪當年被誣陷為告密者而遭到殺害,而真正通風報信的人始終存在於這個家裡,幽靈既是逝者,也是活人。
林玉珍慎重道:「直到主角父親過世後,煩擾母親的幽靈終於消失。全書試圖拼湊的家族歷史也終於瓦解,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卻是一代傳一代的傷痕。」
一同進入墓室的重疊生命史
如果《在黑暗中閱讀》將個人生命經驗映照於歷史,那麼《秘密經文》將主角限縮在愛爾蘭新教徒,揭露新教徒悲慘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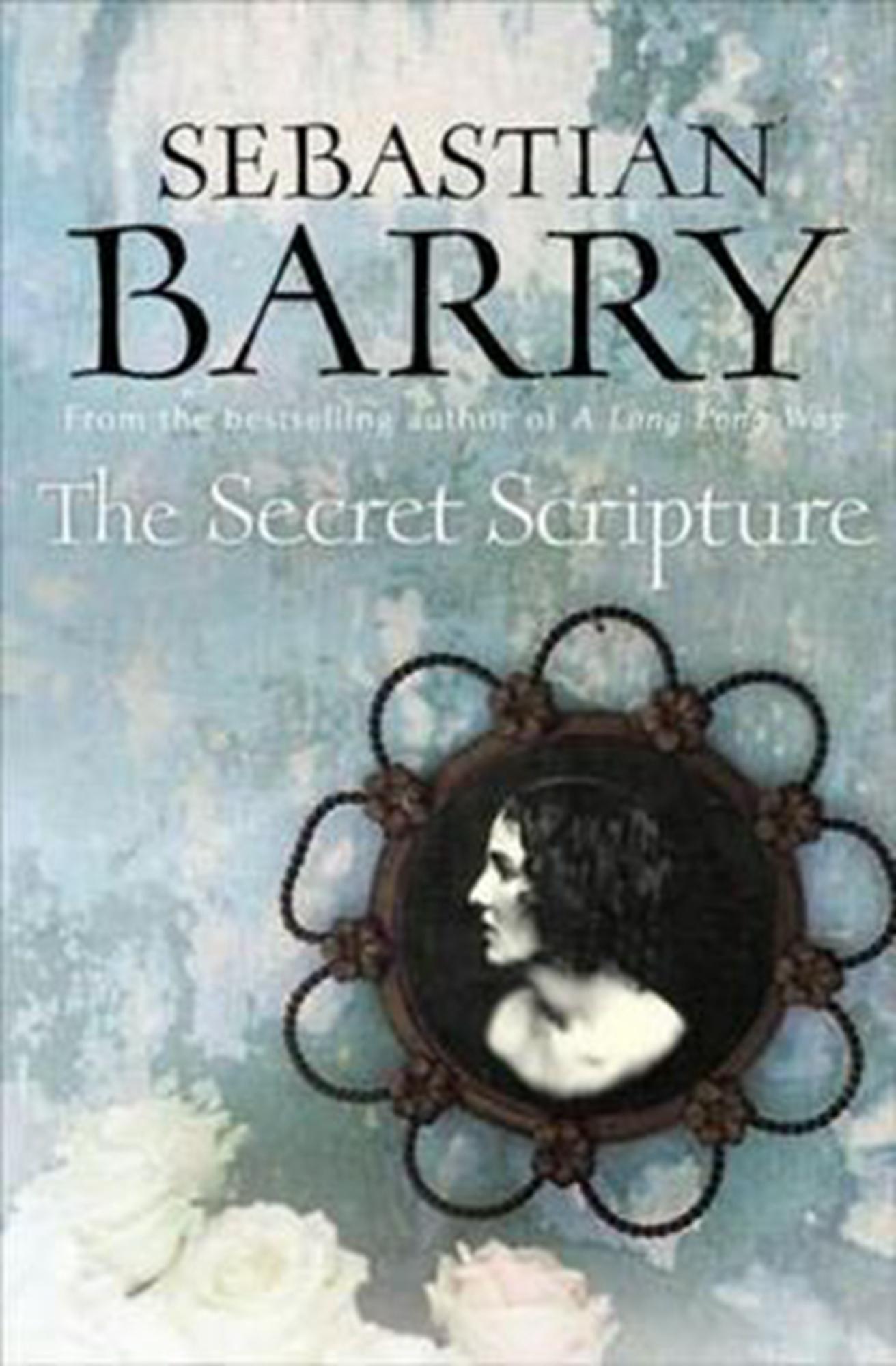
這本2008年出版的小說,故事在主角翁若珊的父親約瑟夫遇害之後展開。約瑟夫某次被帶往高塔,遭到國族主義成員施暴與吊死;若珊卻只記得她與父親一起進行的榔頭和羽毛重力實驗,卻沒意識到榔頭也是暴力的工具。
父親過世後,若珊與戀人湯姆的哥哥陷入熱戀,陰錯陽差之下被誤以為跟其他男子出軌,從此若珊的命運急速下降,甚至與湯姆的哥哥發生關係,在生下一名男孩之後,若珊被送進精神療養院,她的過往也等同於被封存在密室。
待若珊居住精神療養院65年之後,決定記錄自己的過往,與國家歷史譜成詩篇。另一方面,精神療養院院長格林最後驚覺若珊是自己的生母,並且發現自己與若珊相似的命運。然而他卻選擇隱藏真相,鎖住不光彩的歷史。
林玉珍提及,這樣矯正國族主義的動作與作者席巴思欽.薄瑞的生平不謀而合。他多以家族前輩的生命經驗為故事題材,開啟愛爾蘭封存記憶的密室,雖然人物的性格稍嫌單薄,反倒強化歷史墓室的牆壁。
以歇斯底里的語氣揭露國族創傷
相較於前兩部針對個人生命經驗的小說,《暮氣沉沉的國度》在1980年出版,為三本書中出版時序最早的一本,而它的創傷經驗則提高到國家層級。
《暮氣沉沉的國度》故事背景設定在1979年,彼岸美國的愛爾蘭社群關注當年發生的北愛爾蘭危機事件,希望製作愛爾蘭共和軍的紀錄片。社群成員抵達都柏林後,經過一陣探聽找到茱蒂絲‧柯藍西——這位曾經在1921年愛爾蘭獨立運動活躍一時的年邁修女。
但經過查探,當年的英雄茱蒂絲、如今卻歸隱修道院也是有隱情的。她曾失手殺死同為主戰派的同志兼妹妹情人史帕基,政府為了掩人耳目將茱蒂絲送往修道院,而她的姊夫擔心茱蒂絲會說出真相,更用電療等非人道方式意圖破壞她的記憶。
58年後舊事重演,原本社群成員要拼湊當年史帕基命案的真相,卻因為茱蒂絲的姪孫女葛瑞妮雅與採訪者詹姆士發生親密關係,葛瑞妮亞的表哥害怕茱蒂絲說出真相影響自己的前途,將詹姆士驅逐出境;愛爾蘭共和軍派系也不滿葛瑞妮亞與丈夫邁可的婚姻,趁機將邁克連人帶車推入河裡。唯一目睹這樁謀殺的就是茱蒂絲,然而因為她過於歇斯底里說出史帕基事件,因此沒人相信她的證詞。就這樣,相隔近60年、關乎愛爾蘭國族主義的事件也無法逃過灰飛煙滅的命運。
林玉珍說:「這本書的書名影射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詩句(“There’s no country for old man”),暗示國族政治左右人民的生活與記憶,當兩者利益衝突時,國家機器不得不訴諸暴力,以精神醫學的名義,將人民監禁於暗房。」

創傷敘事的自喻與治癒
三本創傷小說敘述人物的「後記憶」(Post-memory)過程,即使經過6、70年,不堪回首的過往仍舊適合放在黑暗當中,試圖釐清事實的下一代人遭遇當事人不可靠的記憶或阻撓,甚至不小心複製上一代的悲劇。
林玉珍提到,這三部愛爾蘭作品,主角都陷入「後記憶」的漩渦之中,他們必須在「真正發生的」、「我所想像的」、「我聽過的」、以及「我一直聽到的」之間取捨,她說:「這也反應了許多愛爾蘭人的歷史記憶,家族或國族秘辛的揭露與否都讓敘事者背負倫理難題,修補家族和國族的歷史傷痛也是一場『再造歷史意識』(refigur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過程,經由重新檢視與不斷修正,釋放跨世代的幽魂。」
然而,愛爾蘭文學只能透過跨世代的幽魂呈現嗎?林玉珍認為不然,她提到在劇場或戲劇呈現這段歷史的作品也不少,受到通俗文化的影響,除了嘲諷的寫實風格以外,也有趣味詼諧的場面。例如《槍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1923)故事:有位作家被其他人認為是槍手,他也理所當然自認為是,直到革命起義軍到他面前,遞給他一把真槍,作家卻嚇得半死,還被另一位女性拯救。此類戲劇有趣的一面似乎也沖淡嚴肅的國族主義與傷痛。
林玉珍強調:「雖然時間不斷前進,但歷史會透過回顧與參照,逐漸照亮過去那段黑暗的歲月。」創傷敘事關懷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在這之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個當代的人們,面對、安撫身處其中的過往,藉此獲得安定的勇氣。
研究來源:
林玉珍(1999-2000)。獨立後的愛爾蘭書寫,1922-1955。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林玉珍(2012)。歷史的夢魘:愛爾蘭當代創傷小說。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林玉珍(2018)。「家中外人」:霸權與獨立後愛爾蘭書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本文授權轉載自人文·島嶼平台,原文連結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