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難民故事背後的吶喊
近年來國際局勢動盪,無論是阿富汗戰爭、敘利亞內戰,還是正在發生的俄烏戰爭,無情的戰火造成大批民眾被迫成為難民。我們常從新聞媒體看見難民的苦難故事,你是否想過難民希望透過故事傳遞哪些訊息?故事本身又如何影響難民的人生?中央研究院 112 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2021 年 8 月,美國結束長達 20 年的阿富汗戰爭,美軍陸續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政權開始接管全境。8 月 16 日,一架 C-17 美軍運輸機載著逃難的阿富汗民眾從喀布爾機場起飛,大批沒搭上飛機的民眾奮力爬進輪艙或緊緊抓住機身,造成多人從空中摔落死亡。
這架平時只能搭載一百多人的運輸機,最後超載了 640 名阿富汗民眾。他們滿心期待奔向美國「自由」的領土,但在降落卡達烏代德空軍基地的那一刻,他們瞬間成為阿富汗「難民」,在前方等待他們的是漫長艱辛的特殊移民簽證申請。
身在臺灣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被迫成為難民的辛酸,但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王智明副研究員發出提醒:
事實上,難民議題並非遠在天邊,難民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甚至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不論是 1949 年國共內戰的大江大海、1975 年越南難民的投奔怒海,還是 1980 年代時有所聞的反共義士,難民都與臺灣歷史的脈搏相應,乃至成為血脈相連的一分子。
為了啟發人們對難民議題更立體的理解與關懷,王智明特別以「難民故事:權利、自由與尊嚴」為題,分享難民之於民族國家的批判意義,並聚焦三部有關北韓難民的故事文本,探討難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脫離身分枷鎖,找回屬於自身的權利、自由與尊嚴。
人們成為難民的原因?臺灣也有難民相關歷史?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22 年 6 月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 2021》,截至 2021 年為止,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高達 8 千 930 萬人,其中有 72% 難民在鄰近國家接受庇護,但這些收容國中卻有 83% 屬於中低收入國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難民人口中,有將近一半(約 41%)是急需援助的未成年兒童。
王智明提到,這些數據清楚指出,難民問題是一個正在發生、亟待解決的國際議題,歐美國家對於相關援助措施已有很多討論,但值得我們追本溯源反思的是:是什麼原因迫使人們逃離家鄉?難民議題與你我又有什麼關聯?

造成難民的原因除了戰爭以外,經濟發展機會的缺乏、極端氣候導致的飢荒、威權政體對生命的威脅等,都可能迫使人們冒著生命危險遠走他國。我們會為逃難途中溺斃的敘利亞兒童落淚,關心俄烏戰爭下失去家園的烏克蘭人民,這些出於人道的情感相當重要。但是難民只是遠在他方的他者嗎?臺灣是否曾有與難民相關的歷史記憶呢?
事實上,臺灣也曾有一段庇護難民的歷史。近期推出的公視紀錄片《彼岸他方》,帶我們回到 1978 至 1988 年的澎湖白沙鄉講美村,這裡曾設立一處「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專門用來收容 1975 年北越共產陣營統一全境後出逃的越南人,10 年間曾收容 2 千多名越南難民。
這些來自越南的難民,多數是在越南討生活的華僑,他們能被臺灣接納,也多半與他們的「華僑」身分相關。他們有些人後來選擇入籍臺灣,更多則再轉移至他國。看似和平的結局卻是一連串問題的開端,進入臺灣社會後,他們究竟是難民還是同胞?是陌生人還是自己人?是苦海求生的平凡人還是反共義士?這些矛盾的疑問凸顯了難民議題的複雜性,背後關乎的不僅是人道救援,還涉及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問題。
難民如何敘述自身故事?故事本身如何形塑難民?
許多敘述難民故事的作品皆試圖探討複雜的難民議題,王智明特別注重的是:難民如何敘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本身又如何形塑難民?就他的觀察,難民的故事通常圍繞著權利、自由、尊嚴的喪失與追尋。
王智明舉詩人 W. H. Auden 的詩作〈Refugee Blues〉為例,傳達難民喪失權利的內心掙扎與尷尬處境。其中一段詩句描述難民試圖入境他國卻拿不出護照的情形:
領事拍著桌子說,如果你沒有護照,在法律上你就算死亡。但我們還活著,親愛的,但我們還活著。
詩中諷刺的指出,一旦成為難民,身分證明文件比人本身更為重要,因此如何取得合法證件成為難民故事的核心關鍵。另一方面,「故事」本身也可能成為協助難民獲救的「證件」,一段動人的故事能讓難民獲得被外界接納、自我療癒的機會。
但是逃難故事的單一化、奇觀化,也可能窄化了難民的形象,遮蔽了難民經驗的多樣性。畢竟難民經驗不是只有逃難這一端,抵達之後的生存狀態亦是難民經驗極為重要的成分。王智明特別選了三部有關北韓難民(脫北者)的故事文本,讓我們從不同視角體會:難民如何被期待去講述一套有既定劇本的故事,以及故事本身如何形塑並影響難民的人生。
三部脫北者故事:從不同視角翻轉難民印象

第一部作品是朴研美寫的《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In Order To Live)。朴研美的脫北故事讓人一窺北韓鐵幕政權下,平民百姓真實的生活樣貌。作者為了逃離北韓,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冰凍的鴨綠江、逃離掮客和黑幫的魔爪、跨越荒涼的戈壁沙漠後抵達蒙古,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搭機飛往南韓。
朴研美的脫北歷程如同一段冒險故事,也是一個相當「典型」的難民故事,符合多數人對難民的既定認知。然而,王智明提醒,並非每個難民都有相同的經歷,但每個人所經歷的痛苦都是無法類比的。
多數讀者習慣用一種「奇觀式」的視角觀看難民故事,藉此激發對難民苦難經歷的同情心。王智明認為這情有可原,因為只有在讀者惻隱之心被啟發後,我們才有可能去理解和同理難民的處境。但王智明也向大眾拋出疑問:
我們會不會因為難民來自北韓、敘利亞、阿富汗等威權國家,因而產生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是在閱讀難民故事時值得反思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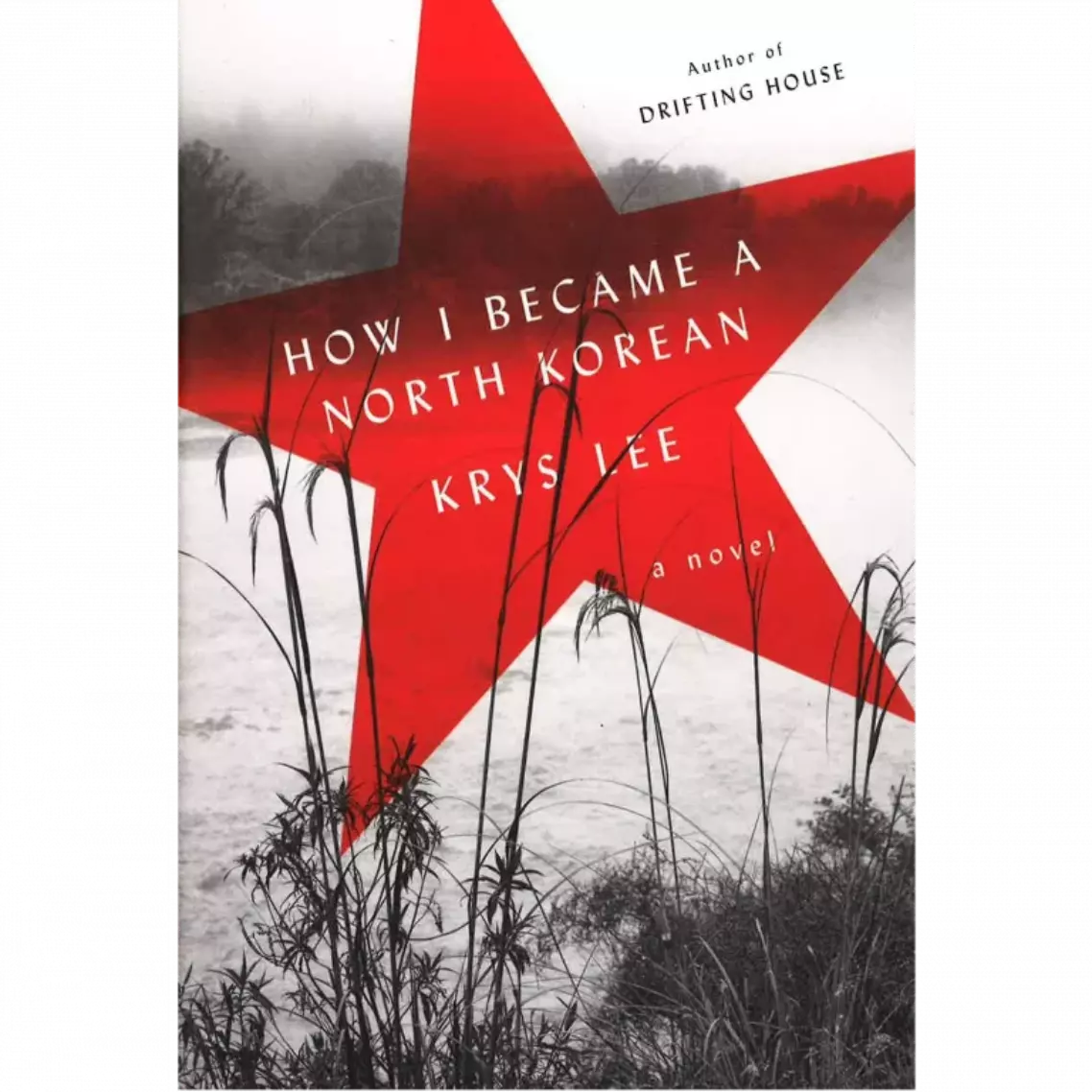
第二部作品是韓裔美國作家 Krys Lee 寫的《How I Became a North Korean》。故事發生在中國和北韓的邊境,主角是一名住在中國的朝鮮人,他曾到美國生活,後又回到中朝邊境。在誤打誤撞下被誤認成脫北者,發生從「移民」變成「難民」的身分錯置。
書中詳實描述脫北者在逃難過程中遭遇的各種威脅。某些女性被迫成為性工作者,或被賣給有殘疾的中國男子為妻。男性則可能受黑幫的暴力壓迫,淪為沒日沒夜出賣勞力的黑工。在中朝邊境中的他們無所依靠,既要尋求日常溫飽,又要躲避警察,只能依賴教會等人道救助團體的協助,但是人道救助並非全然無私。
王智明發覺,這部作品最特別的是,翻轉了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刻版印象。看似拯救者的教會卻是脅迫者之一,以向警察檢舉來威脅脫北者信教。看似被拯救者的主角,最終還是得靠自己的力量恢復自由身,並拯救其他脫北者。更關鍵的是,當他們成功抵達南韓之後,脫北者的身分並未隨之褪去,反而纏繞其身,成為恐共的南韓社會歧視他們的理由。

第三部作品是韓國作家 Cho Haejin 寫的《I Met Loh Kiwan》。故事的主要敘述者是一名韓國記者,他受到脫北者 Loh Kiwan 的啟發,踏上一趟追尋難民經歷的旅程。故事重點不在敘述脫北過程,而是聚焦探討脫北者來到異國後的生活。
故事的敘事者亦步亦趨地來到比利時,探訪 Loh Kiwan 曾落腳的地方,感受與思考作為難民的他曾遭受過什麼樣的待遇,如何以極為有限的資源度過初到比利時的每一天。包括被旅館的接待人員白眼和冷待,保存早餐的麵包作為一天的食物,沒有工作與方向,面對自己饑餓與他人幸福間的巨大落差,以及在異國語言和文字裡的苦苦掙扎。
「Loh Kiwan 在此化身成一個象徵、一條線索,讓讀者投身在難民經驗中,走一遍難民到異國後可能遭遇的經歷。」王智明點出該部作品在敘事角度上的特殊之處。
故事結局相當振奮人心,Loh Kiwan 在餐廳遇見一名菲律賓難民,她得到去英國的機會,而 Loh Kiwan 也願意一同前往。他們看似拋棄在比利時好不容易獲得的安穩生活,事實上正逐步擺脫被援助者的身分枷鎖,靠自己的力量去學習新語言、適應新環境,如同一般人一樣擁有真正的尊嚴。
「我們只想活得像個人!」撕掉刻板標籤,看見故事背後的真實訴求
這三部作品呈現了不同的敘事視角,包括難民的自我表述、既定認知的翻轉、難民異國經歷的反思。經由閱讀這些故事,我們對難民的認識,將不只停留在「受援助者」或「被同情對象」等刻版標籤之中。
王智明更提出另一個認知陷阱,也就是脫北者常被放在反共敘事下來理解,脫北行動代表反對獨裁的金氏政權、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但是當脫北者真的來到民主國家後卻發現,他國政府與人民並沒有想像中的寬容,反而要求脫北者服膺特定的反共義士形象,更在無形間將其「他者化」,在公民與難民之間劃出一道界線。
朴研美曾提到當初決定脫北的原因:「我們只想活得像個人!」沒有人願意成為難民,通常也不是為了特定政治目的,多數人只是為了追求可以「活得像個人」的基本人權。然而,所謂的「人權」卻是說的比做的多,雖然聯合國人權公約有明文規定保障所有人類的權利,卻少有國家可以明確執行。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沒有了公民權,也就沒有了人權」,但真正能取得公民權的難民通常少之又少。面對人權的弔詭,鄂蘭甚至刻意主張:「難民最需要的就是名聲,什麼樣的名聲都好,只要能鬧事、被看見,就有爭取權利的機會。」
換言之,那些沒被看見、聽見的難民,就沒有被理解的機會。雖然難民的故事可能將難民「他者化」,但王智明認為,我們更應該關注故事背後的情感和聲音,因為這些聲音恰恰是難民訴求被聽見的機會。
在演講的最後,王智明將難民議題再次拋給眾人反思。在臺灣這個由多元族群組成的移民社會,我們正面對美中勢力多方較勁、臺海周邊詭譎多變的局勢:
我們都是外來者,我們也可能成為流亡者。希望他們的故事不會成為我們的經驗。
期許眾人能透過不同的難民故事,與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建立聯繫,看見權利被長期忽視的族群,喚醒我們對人權與正義的關懷。當我們能進一步理解並尊重難民的經歷,認真思考造成難民傷痛與移動的歷史,才有化解歧視、寬容接納外來者的可能,實踐真正的社會正義。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文請<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