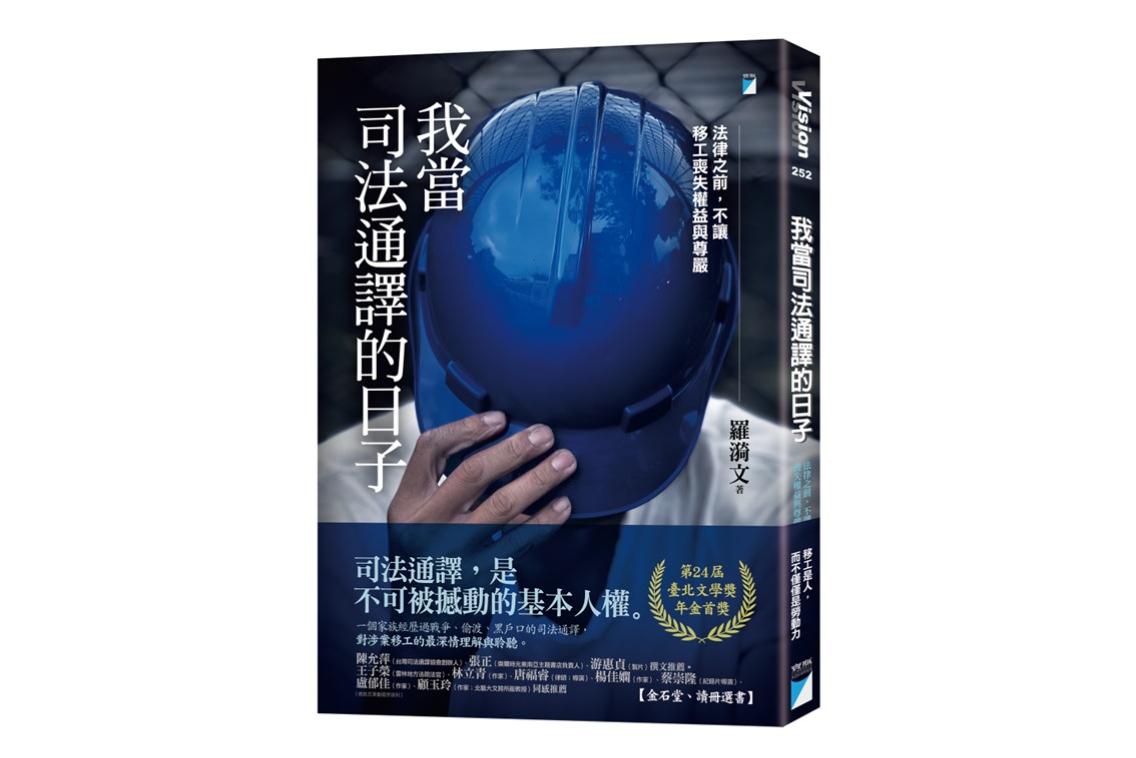究竟是什麼,讓人跟人之間被切割出不同?
是命運嗎?是社會階級?是教育體制?還是全球化?
每學期開學的第一天下課,我都會趕赴龍山寺的晚課,站在廊簷下靜靜聆聽,悠揚的誦經聲夾著清脆的鐘罄聲在庭院起伏飄蕩。迴廊兩側台階坐滿了老年人,虔誠地手持經文小冊子跟著唱唸。
年復一年,晚課結束就立刻離開前往捷運站,完全不知道寺廟旁邊就是鼎鼎大名的華西街夜市。
越南美甲業成群進駐華西街
疫情被攔阻在台灣以外,但春天尚未到來,淺灰的天色讓人突然有股衝動想要在附近走走,於是才發現了華西街。
紅色的仿古牌坊大門勾起了稀薄的回憶,似乎是剛到台灣時候,表哥曾帶來參觀過。但不見傳說中生猛的蛇肉店,筆直的商店街兩側盡是美甲店,幾乎是隔兩三間就一家,霓虹燈招牌點亮著「越美」、「妘莊」、「紅絨」等等名字,是中文卻又不屬於台灣風格。
我帶著微微的驚訝努力尋覓著,終於看到乏人問津的店面門口有一個玻璃櫃,櫃內躺著一條塑膠小蛇,明確告訴我一個時代早已消逝。
這感覺有點像香港九龍半島上的重慶大廈,老舊大樓內的香港本地人離開了,取而代之是非洲人與南亞人聚集。他們採購二手貨和廉價成衣運回家鄉販售,形成了人類學家研究低端全球化現象的著名案例。
而今華西街夜市迎來了越南美甲業成群進駐,上演新一輪激烈的生存競爭。修剪指甲費用壓低至兩百元以下,相當於越南非觀光區域的價格。
在疫情之前的夏天,我和朋友前往越南,鼓起勇氣進入胡志明市中心歌劇院附近的美甲店,選了最基礎的修剪項目。然而,因為不習慣被人捏住腳趾和手指,我渾身僵硬起來。
負責替我修指甲的小姊姊於是尋個藉口落跑了,移交給一位溫柔小弟弟接手,那次的美甲收費折合台幣兩百五十元。
台北古老的龍山寺多幾抹東南亞風情
華西街的美甲店內不只有年輕女性顧客,還有中年婦人與年長阿伯,也坐在寬大的仿皮單人沙發椅上,單手或單腳泡在小水盆裡,另外的手腳則被坐在矮凳上的女子握住,進行著仔細的維護。
我難免刻板印象地以為上了年紀的男人們怎麼可以紋眉、美甲,原來是我錯了,便宜的越南美甲隊伍正在改變台灣人的消費習慣。
甚至,美甲愛好也可以搭起親切的橋梁。
記得某一次的偵訊,年輕的專勤隊女隊員,左手戴金色手錶,右手戴藍藍綠綠的水晶串珠,指甲彩繪寶藍色的圖案,非常可愛。
當事人是越南女生,被請來釐清婚姻仲介一事,指甲也是多彩繽紛。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十分爽朗活潑。
筆錄結束後,兩位女生互相讚美對方的指甲彩繪。我幽幽插話:「我看到你們指甲上的圖案了,好漂亮喔!」
我在美甲大道來來回回逛了兩次,數了又數店家的數目才慢慢踱步至捷運站。
天色已晚,漫天烏雲低低壓在頭頂,冷風中傳來些許越南語音。我轉頭四處張望,人行道上站著幾名濃妝豔麗的女子,正以越南語聊天。
龍山寺四周明明是台北的古老區域,現在多了幾抹東南亞風情。
是什麼讓他們不一樣呢?
對華西街變遷的感嘆可能一直是淺淺的,如果不是在數天以後的一次通譯,我才意識到我已經居住了三十年的城市,還有其他明暗相間的複雜紋理。
專勤隊前一週就預約我某日的早上七點鐘,後來打電話取消,說他們昨夜守到兩點,仍一無所獲,但也請我準備夜間再來,因為他們還會去抓人。
果真,凌晨十二點左右,同時有兩通電話打來,催促:「抓到人了,快快來!」
匆匆抵達時,還有其他語種的通譯也在現場。專勤隊員忙碌搬出兩張長桌併一起,闢成一個臨時報到區。
有人從外面大聲通報:「車子回來了!」隊員們陸續扛著一袋袋裝著電腦主機和螢幕走進來,喊:「這是扣押的證物。」
接著是一群人被快速帶到辦公室的最深處角落。清一色是年輕女孩,打扮很不錯。「逃跑外勞有穿這麼整齊時髦的嗎?」我坐在一張空著的辦公桌前,看著眼前的景象,卻後知後覺地想著。
跟我比較熟的小隊回來了。大家一臉疲憊,但開心地跟我打招呼,隨即迅速徹退,「回去睡一下,早上八點還要來接班。」
確實不是普通的逃跑外勞,是萬華的應召站被查獲了。
來專勤隊通譯多次,難得看到整個大隊的四個分隊全員到齊,連同被抓來的十二位越南和泰國女生,七、八個台灣年輕男生,萬華警察局人員,讓寬大的辦公室變得十分熱鬧。
專勤隊員大多數正值青春年華,雖每個人都戴著口罩,仍然看出有些女隊員額頭飽滿,眉眼明亮,應該是長得秀麗好看的人,而那些被帶進來的女生更是婀娜嬌美。
我忽然感覺到絲絲奇異,究竟是什麼,讓人跟人之間被切割出不同?
這是特殊專案掃蕩,屬於現行案件。按照法律規定,現行案件須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移送法院,因此作業時間十分緊急。
專勤隊人員直接在辦公桌前進行詢問,我在一旁協助翻譯。
做筆錄的中途,萬華分局的年輕警員跑來跟女生們,收取違反「社會維護法」的罰款,並請她們簽放棄抗告書,隨即帶著逮捕到案的四個「馬仔」揚長而去。
警察們散發著英挺慓悍的氣息,而馬仔們也䠷年輕,「沒有比我的學生大多少嘛!」我想起正準備赴美深造自然科學博士學位的學生,是什麼讓他們不一樣呢?是命運嗎?是社會階級?是教育體制?還是全球化?我真是困惑了。
不怪應召站,要怪就怪第一次邀她來台灣的人
從事特種行業的筆錄會問得相當詳細且反覆:這工作做多久了?每天接多少客人?每次多少錢?怎麼跟應召站拆分?
然而,讓我一時卡住的是「半套」,還是「全套」這類「術語」。我搜遍腦袋,找不到越南語的對應詞,於是拜託筆錄人員解釋清楚,再以越南文說出「依法律定義,所謂半套是這樣,全套是那樣。你是做哪一種?」
因為問得太過私密,自尊心受到刺激的長髮女生一邊回答,一邊哭泣。有時還會生氣:「怎麼一直問來問去,剛才已經回答了啊!」
專勤隊員回嘴:「你不要生氣,我們也很想快點結束好不好!」
長髮女生從下午四點工作到凌晨四點,平均接待七至八名客人。半套一千兩百元,應召站抽五百元,只是她時常生病休息,所以從耶誕節開始做到現在,除了有兩支iPhone手機,總共才寄了十八萬台幣回老家。
「因為媽媽生病了,需要錢看醫生。男朋友薪水低,沒幫得上忙,只能載我上班和下班。」
我翻譯專勤隊員的問話:「你逾期居留要被罰一萬元,還要自費買機票回去,你身上有錢嗎?」
女生反而問我:「沒有那麼多。姊,我可以跟你借錢嗎?我回越南,再寄來還你。」
我默默在心裡吶喊:「妹子啊,姊是月光族哩!」
把她的前半句答話翻譯給專勤隊員聽,再把專勤隊員的問話翻譯回來:「你的男朋友呢?他可以借你嗎?」
女生說:「他很窮的,我再跟其他被抓的姊妹借好了。」
問:「她們會有錢嗎?她們自己還要繳罰金啊!」
答:「有啦,她們都有錢。」
專勤隊員追問:「有沒有被脅迫、拘禁、餵毒品控制?」
女生搖頭。
工作很自由,要做就做,不做就請假。一次賺七百元,挺好的。之前曾短暫在屏東農場種菜、剪辣椒,一個月三萬五千元。
不怪應召站,要怪就怪第一次邀她來台灣的人,那時說是農場工作,結果不是,現在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趕時效的偵訊一個接著一個,我也「轉檯」,換至下一位需要通譯的對象。
是不是在異國很孤單?也可能難過被驅逐出境以後,就沒辦法賺錢給媽媽。
我離開時,她依依不捨地望著我。
只是,我又能怎麼辦呢?
通宵達旦,終於完成所有筆錄。
最後要把證物放進袋子封緘,無奈沒收來的手機是最新型號,專勤隊員大喊:「iPhone 12要怎麼關機?誰會關iPhone 12?」
大家問來問去,我有點緊張:「我是用Android的喔!」
終於有人跑過來協助關閉電源,專勤隊員喃喃:「真是太高級了,沒用過這麼高級的手機。」
我望著眼前的一排辦公電腦,螢幕周邊貼滿可愛的紅色春聯:「我要好多錢!」「誠徵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看來大家都有共同的心聲,賺錢真是太難了呢!
我又來到龍山寺,但中庭空蕩蕩的
時序轉進初夏,媒體報導,木柵一位老先生前來萬華買竹筍,疫情於是驟起。進行了三分之二的學期,突然被迫改為線上教學。學校在熱區附近,無法回家的學生只好待在宿舍裡。
我們對著電腦螢幕上課,學生說:「老師,我去學校小七買食物回來,都會用酒精把便當盒噴一噴。」
沉寂而疏離的暑假過去,開學了,線上教學維持兩週才恢復實體教學。
我又來到龍山寺,晚課依舊,但中庭空空蕩蕩的。
往常四處走動,維持秩序的阿伯戴著口罩,語調有些惆悵:「人真的少了很多!」
秋季的陽光照耀著寺廟兩側的鐘鼓樓,金色的觀音在正殿內莊嚴安座,目光肅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