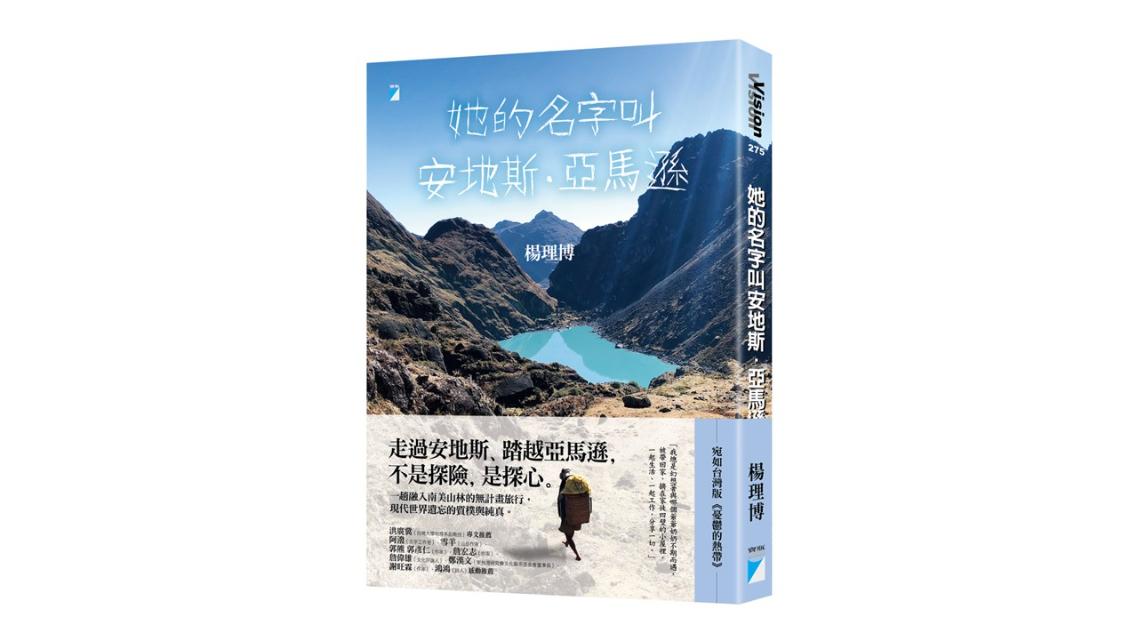我從裹了五層厚重毛毯的床翻身起來,縮瑟著身子,透過屋裡小小的玻璃窗往外看,遠方天際線被染成漸層的粉紅與紫藍,天地間好像不存在分野。打開窗,空氣如冰河湧入,一個從阿拉斯加一路騎單車南下的美國旅人告訴我們,這裡晚上的室外溫度是零下十五度。而此時,奶奶已經坐在院子裡的爐灶邊,生火做飯了。
來到爺爺奶奶家就是一場意外的際遇。我們搭上了同一台便車,當時車上座位已滿,我原想讓座,但爺爺比我飛快地跳上行李倉,探出一顆頭,靦腆地笑著跟我們打招呼。一路上車裡的人以Aymara語輕聲聊天,卻聽得出來聊得熱絡,偶爾轉成西文好奇地問我們各種問題。聽到我們還不知道今晚住哪,奶奶毫不猶豫地答應接待我們。
一場便車的命運交會
爺奶的家在高原上,一口快乾涸的大湖邊,一座快廢棄的小村子裡。在聯外的土路開通之前,他們都是靠驢子搬運馬鈴薯,走半天的路到最近的小鎮交易生活物資。一年前這條路開通了,村民們都紛紛搬到鎮上,爺奶成了村子唯一的常住戶。
高原冰寒而明亮,地球在這裡脫下了所有外衣,赤裸裸的黃土攤在藍天下。爺奶住在刷了白漆的土屋裡,屋前有個大院子,院子裡一口土爐子充當廚房。日子辛勞,卻活得很開朗,尤其是奶奶,笑聲中氣十足,雖然五個孩子都搬走了,但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同住。家裡唯二對外的通訊,是一台太陽能收音機跟按鍵式手機。每天的例行工作就是早起把羊群趕到不同草場,傍晚再趕回家;趕羊時,順便在光禿的大地上搜尋可供燒火的枝條、推著單輪車到村裡唯一的水井取水。生活如是,日復一日。
爐上的鍋子早已咕嚕作響,我打著哆嗦來到火邊,跟奶奶道了早安,坐在羊毛皮墊上一起削起馬鈴薯皮。
chairo熱湯裡的日常:在高原煮馬鈴薯
早餐吃的是chairo熱湯,也是奶奶最常做的一種料理,因為天氣太冷了,有時候一天三餐都吃chairo。Chairo的主角是馬鈴薯與馬鈴薯凍乾。馬鈴薯是安地斯山區的傳統主食,能適應高原氣候,卻不如穀物耐放。新鮮採收的馬鈴薯必須在幾個月內吃完,但安地斯民族千百年前就發現了這片土地的生存之道:將馬鈴薯製成凍乾。方法非常簡單,馬鈴薯只要在這個季節放在空曠的室外,晚上結凍,白天再日晒融冰,就會變成像吸了水的海綿,此時用手擠就能將水分壓出,如此反覆操作個四、五天後,就會變成像發泡煉石質地般的凍乾,可儲放好幾年。
而在安地斯鄉村的廚房裡,通常不會有砧板或削皮刀這種東西,但又以馬鈴薯為主食,所以我很快也學會一把小刀在手就可以將薯脫皮切塊。石頭也是重要的廚具,以扁平微凹的大石為基座,再以石塊滾磨或敲擊,特別適合用來處理預先泡水軟化的凍乾,如此丟進鍋裡很快就煮熟了。奶奶的chairo裡還會加入一些穀物、蔬菜及肉乾一起燉煮。因為天氣乾冷,所以獸肉只要稍微日晒風乾後,放在土屋裡就可以保存,家裡的倉庫有整水桶燒過毛的羊頭與羊腳。
奶奶將已經滾一陣子的湯鍋打開,加了點鹽巴調味,盛了滿滿一碗的chairo,還特別挑了一隻羊腳,熱呼呼地遞給我。寒冷的高原之冬,太陽在我手中緩緩升起。
五彩馬鈴薯與土石廚房的日常
冬季正是馬鈴薯採收之時。那天爺奶讓小女兒一個人去顧羊,便帶我到田裡一起採收馬鈴薯。爺爺先用鏟子把一株株枯掉的馬鈴薯植株鏟起來,我跟奶奶就坐在地上掏薯。爺爺說今年雨水少,馬鈴薯都長得很小,但我卻驚豔於挖出來的馬鈴薯色彩斑駁,有白、黃、粉、紫、黑,每一種爺爺都可以叫出一個名字。
我們就這樣在田裡工作了一整天,清晨還天寒地凍,正午的豔陽卻又讓人無處可躲,如此嚴苛的環境中,馬鈴薯卻代代繁衍生息。
馬鈴薯可以說是安地斯山送給世界的禮物。安地斯民族很早就馴化了這項植物,並依賴它在高原中生存。西班牙人來到這片土地後也發現這項植物的耐寒、耐旱、耐瘠,將之帶回舊大陸,很快就成為許多貧困地區的主食。[…]直到現在,馬鈴薯依然盡忠職守地陪伴在安地斯民族的日常,幫助爺奶度過一個個旱年。
黑夜降臨之後,大地再度冰凍,不想變成凍乾的我們只能依偎在火光的結界裡貪圖一絲溫暖。奶奶看我穿得單薄,特地拿了一件她織的羊駝毛毯,要我裹在肩背上,胸前再用別針別起來。爺爺看了一直笑,因為這在當地是婦人的裝扮。
我不以為意地繼續削著馬鈴薯皮,爺爺在石磨上敲打著凍乾,奶奶則到倉庫裡拿了幾隻羊腳,然後全部一股腦丟進鍋裡。那裡頭就像濃縮的高原:馬鈴薯、馬鈴薯凍乾、羊駝;沙土、湖水、寒氣與陽光。
等待之間,爺奶用Aymara語有說有笑,我不時聽到我的名字參雜在對話之中。我猜他們是在開我玩笑,因為白天工作時,爺爺一直跟我說太小的馬鈴薯不要,埋回土裡讓它之後發芽,但我還是忍不住留了太多指節大小的馬鈴薯。「他們可能是在笑說,以後這種小馬鈴薯要叫papa Lipo吧。」我心裡想。
「奶奶說她以後死的時候,Lipo會為她哭,」爺爺突然改用西班牙語跟我解釋,「這裡的年輕人都搬走了,只有台灣來的小夥子跟我們一起工作。」說完,我還沒來得及反應,爺奶看我一臉呆,又開始大笑,那笑聲被風帶走,流散在空曠的大地。
因為我們必須進城一趟辦理簽證,所以我跟爺爺提議由我們包一台車,順便也載孫子跟女兒們回小鎮準備上學上班。爺爺聽了頻頻點頭稱是,臉上的表情卻若有所思。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個提議對這高原上的一家人來說像個大事一般,一早起來,家裡的節奏就跟平常大不相同。
孫子們躁動不安,在院子裡裡外外嬉笑狂奔,還常常飛撲在沙土地上打滾。最後他們意氣風發地踱步回來,我才看到他們手裡擒了兩隻瘦巴巴的雞。
家裡的雞比較像是鄰居,大部分時候都跟人保持著一種點頭之交的禮貌距離,看似閒散地四處散步,其實覬覦著晾晒在院子裡的穀物。當牠們露出馬腳,爺爺會飛快地丟石驅趕,雞立刻哭喊著落跑,遠離後又馬上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漫步在沙土裡挖蟲,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偶爾爺奶會撒一些玉米給雞吃,這就夠牠們甘心與人為鄰了。
奶奶將孫子們抓回來的雞斷喉放血,然後交代女兒跟小魚午餐的工作,便匆匆出門。
爺爺在家也沒閒著,把奶奶前一天炒好的小麥粒放到手搖的研磨機中轉起來。這種手搖式研磨機在安地斯山上的偏遠鄉村可是家戶必備的農具兼廚具,各種穀物都必須靠它製粉才方便料理食用。
爺爺正在製作的這種小麥熟粉很像我們的麵茶粉,沖熱水就可以直接食用。在日夜溫差極大的高山地帶,一頓熱呼呼的早餐至關重要,所以安地斯山間的晨間市集裡總會有包得圓滾滾的婦女推車兜售穀漿,再配上炸麵餅,溫度與熱量兼具。而穀漿的種類包羅萬象,除了有國際化的小麥、大麥、玉米、燕麥等等,也有近年來在有機商店火紅的安地斯傳統作物藜麥,以及較少為人知的藜麥的另外兩個好姊妹:kiwicha及cañihua,同樣色彩如寶石般豔麗而且營養豐富。
我跟爺爺兩人輪流轉著研磨機,手搖其實相當吃力,不到幾分鐘手臂就痠了,而要磨到足夠的細度,還必須磨兩次。我們終於磨完兩大袋的粉,爺爺一邊用繩子綁口封好,一邊叮囑我到村裡的水井去找奶奶。
原來奶奶早已在水源旁架起了簡單的石灶,燒起大鍋的水,將家裡所有的衣物都用單輪推車推了過來,準備洗澡洗衣。一見到我們,奶奶立刻下令要我們把身上的衣服全脫下來洗。
因為高原氣候乾燥寒冷,我們已經許久沒有洗衣服了,再加上天天都坐在沙土裡掏馬鈴薯,當我把外衣放進水桶,還沒搓,水立刻變成黑的。小女兒看了大笑,開始如大聲公的循環播放功能幫我散布消息。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反正能在寒冷的高原上洗個熱水澡,趁著日正當中把自己跟衣服都好好晾晒一番,我甘之如飴。
中午非常難得,吃的是香噴噴的白米飯配大塊雞肉。在這裡,米需要到城裡買,輾轉好幾趟運回家裡,所以家裡很少吃白飯,孩子們都特別興奮。雞雖然燉煮了一個上午,但肉依然非常結實。平日若是我跟小魚在外面的市場吃飯,我通常會把雞骨頭也都啃食乾淨,但我這會卻發現,這放養雞的骨頭是硬到啃不動的。我對這些雞升起由衷的敬意,在冰寒高原上自由自在的生命,果然風骨硬挺。
爺爺吃過午餐後又繼續他的工作,備好四個布袋的馬鈴薯跟馬鈴薯凍乾,以及好幾個羊毛皮墊。最後所有工作都忙完後,爺爺才到水源處去洗澡,回來後換上奶奶手織的白色羊毛長褲。
「帶這麼多東西,是要進城賣嗎?」坐在院子裡等車時,我問爺爺。孫子們在一旁玩起一顆破洞漏風的球,早把剛換上的乾淨衣服又都弄髒了。
「不不,我們要去旅行。我順便安排了一個工作,會在鎮上待一個禮拜。」
什麼工作爺爺也說不清楚,但讓我驚奇的是他們對這趟短短的旅程所做的準備。對我們來說,旅行很輕鬆,出發南美洲之前我跟小魚只各背了一個背包,背包裡塞的也大概就是平常爬山會帶的東西,然後就飛過了半個地球,來到這個高寒之地。但對爺奶來說,只不過是到附近的小鎮一趟,就像遊牧民族的季節遷徙一樣,要準備這麼多的糧食與物資,更別說那些隱性的心理準備了。
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人們都移居到城裡時,爺奶仍然選擇留在這裡:因為他們的生命是根植於這片土地的,就算只是暫時離開都不那麼容易。這裡有他們的馬鈴薯田、他們的羊駝、他們的草場、他們的聖山,所有身體與心靈所仰賴的一切,都在這片土地上,無法連根拔起帶走。
其實所有的生命都一樣,是屬於大地的:植物必須往土地建立根系,動物們也有固定的領域範圍;一旦離開故土,生命就會受到威脅。然而現代文明動物的我們,已經將地表上的許多地方標準化、模組化了,所以可以輕鬆地將自己習慣的生活複製一份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就像電器一樣,隨插隨用。
我很羨慕爺爺奶奶仍然保有這條與土地相連的臍帶,名副其實地供給他們生命的養分。當然我也很享受現代經濟模式所帶給我的旅行自由,讓我能看見這個地球更完整的樣貌。對我來說兩者沒有優劣之分,反倒是同時看見兩者之後,讓我更能欣賞與感謝我當下所擁有的。
出發之際,爺爺慢慢將行李搬上車,然後拿了一袋馬鈴薯出來,放到我面前說:「這袋馬鈴薯給你們,你們在路上肚子餓了就煮來吃。」沒有多說什麼,爺爺轉過身繼續整理他的行李。
後來回想起來,那天我們吃的那兩隻雞,是爺爺奶奶特別為我們殺的。在我們後來的旅途中,我發現常常我們跟一戶人家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後,離別時,家裡都會特別殺一隻雞。那好像成了一種共通的語言,沒說出口,卻往心裡去了。